《师生会客厅》缅怀余光中
余光中先生1928年10月21号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因母亲原籍为江苏武进,故也自称“江南人”。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I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 21 种;散文集 11 种;评论集 5 种;翻译集 13 种;共 40 余种。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诗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散文集)及《分水岭上:余光中评论文集》(评论集)等,其诗作如《乡愁》、《乡愁四韵》,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
余光中在现代诗、现代散文、翻译、评论等文学领域均有涉猎。作家梁实秋曾称赞其“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在这个许多人不读诗的时代,余光中却是一个“异数”,他的《乡愁》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每个中国学生必读诗;而他的《乡愁四韵》等诗被谱上曲子变成歌,同样传唱到海峡两岸、大江南北。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令人想起了许多事情。”余光中说他读过、写过、译过相当多的抒写火车的诗,他最喜欢的是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这一首。探究一下余光中的内心世界,抑或是那一声凄苦长啸的汽笛,唤醒了诗人绵长而沉重的记忆吧。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诗人如是说。
余光中记忆深处铁轨上的第一颗铆钉,当是九九重阳节。“谁言秋色不如春,没到重阳景自新。随分笙歌行乐处,菊花茱萸更宜人。”重九登高,两千年来绵延不绝,典出何处?据余光中考,源之《续齐谐记》中记录了一个家族为避灾祸,盛茱萸囊饮菊花酒登高的故事,一个美丽而哀怨的传说。
1928年的重阳节,美丽的少妇孙秀君偕同亲友攀南京栖霞山登高眺远,动了胎气,次日凌晨产一男丁。族人命名“光中”,光耀中华之意。母难,令余光中的“寸草心”终有难报“三春晖”之恨,但他很自豪自己的生日,那毕竟是个诗和酒的日子,菊花的日子,茱萸的日子。余光中得意地自称为“茱萸的孩子”。
余光中,祖籍福建泉州永春人,著名的侨乡之乡。母亲孙秀君江苏武进人。在常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福建永春任教,与时任县教育局长的余超英结为伉俪。余超英后供职于民国政府专事侨务。“茱萸的孩子”生于人文荟萃的六朝胜地金陵,十代名都的灵山秀水浸润着他的豁齿童年。
然而,记忆又像铁轨那样凄冷。
往事知多少?童年的花瓣还未尽绽放,却被战争的硝烟骤然卷去。“故国不堪回首”,烙在余光中记忆中最深的印记是做亡国奴的悲哀。炮声一响,父亲旋即随机关撤往武汉。母亲携着九岁的余光中随着逃亡大军从南京城里到常州乡下,旋经陶都宜兴、太湖渔村,萍飘四处。
为避日寇追捕,他们母子或藏身佛寺大殿的香案下,或躲在路边败垣残壁的阁楼上。绝望之中搭乘一条运麦的民船逃往上海,孰料船过鼋头渚撞上了宝丹桥,翻舟覆顶,幸大难不死,总算到了上海滩,寄居在法租界友人的屋檐下。
余光中要上学了,租界是洋人的世界,要学洋文,只靠母亲为他做英文启蒙教育。烽火三月,幸而接到万金家书。远在重庆的父亲希望他们去团聚。次年,由水路经香港,绕道越南,再由昆明辗转万里始到山城重庆。
江南少年的余光中成了川娃子,他进了由南京迁来的教会学校青年会中学。校舍是借用的破败的民宅,但他在这里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学校里的孙良骥老师,家中的二舅,把他搀引入古典文学殿堂。韩潮苏海的圣贤文章陶冶了他的身心,英文也大有长进。经一番风霜,在校内语文竞赛中,余光中脱颖而出,“光耀校中”,英文作文第一、中文作文第二、演讲第三。
战时书籍匮乏,他向一位同窗借得一本《英汉大辞典》,强闻博识,恨不得鲸吞。一次富家子弟们聚首斗阔,余光中好胜挤入“露一手”,他问谁知道一个英文单词最多有几个字母。无人敢接招。余光中一口诵出一个由二十九个字母组成的单词,语惊四座。
那时,余光中学业偏科,考语文,他为同学捉刀;考数理,同学给他打派司。不知何因,他对地理的兴趣特浓,爱读地图,把地图当作《圣经》来读,以至形成他终身收藏地图嗜癖;同时,亦钟情天文、绘画和翻译。后来翻译了《凡•高传》,博得盛名。
国人八年浴血,终获正果。抗战胜利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归故土。1947年他高中毕业,同时报考北大、金陵大学,双榜题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余光中有太深的恋母情结,为依母膝,他选择了金陵大学外语系。
此时,他曾受教于吕叔湘先生帐下。吕先生朴素清纯的译风使余光中受益终身;那时他还常聆听冰心、曹禺的讲演……大一的那年,余光中牛刀小试,翻译了拜伦、雪莱的诗作在报刊上发表。痛心的是内战狼烟又燃,他在金陵大学仅读一年半,复流离上海、厦门。在厦门大学学生会主办的一次“各言其志”座谈会上,他第一次表白心迹:“我将来要当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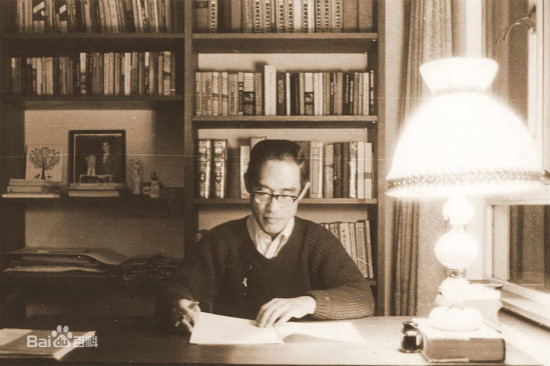
国事蜩螗。1947年他滞港辍学一年。1950年就读台大外文系。在文风颇盛的台大,他成为黎烈文、赵丽莲、曾约农先生的高足。曾先生是曾国藩之后,他的开明与宽容,教余光中铭感五内,先生竟允许他以译文《老人与海》充作毕业论文。更令他难忘的是有幸亲炙梁实秋。
经同窗好友蔡绍班介绍,将余光中的诗作转请梁实秋圈点。梁实秋读之,觉得此后生可爱,前途无量,亲笔复信鼓励有加,同时指点迷津:“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些现代诗,例如哈代、浩斯曼、叶慈等人的作品。”
余光中受惠欣喜不胜,旋登门拜师,梁实秋一心奖掖,余光中不负厚望终成诗文大家。这对师生之谊酝造了一曲文坛师生的佳话。是时,余光中经常向《中央日报》、《新生报》投稿,每稿必中,声誉鹊起。
大四的那年,余光中出版了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他恳请梁实秋作序。而梁实秋潇洒,竟以一首三段格律诗充之。余光中怏怏,斗胆上门宣泄怨绪,说先生的诗没有针对自己的集子写。梁实秋很大度,淡然一笑,说以后再写一篇书评弥补吧。梁实秋果然践诺,写书评,对余光中的诗作中旧诗的功底和对英诗营养的一并汲取的创作方法予以肯定。他认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线路。”
余光中一直称梁实秋是“恩师”。他为梁实秋八十七岁华诞编了一本《秋之颂》,1987年梁实秋突然西去,次年梁实秋冥寿日,余光中在梁墓前,三次点火将五百七十八页《秋之颂》焚祭,祈祷恩师在天之灵。曾有评论者说余光中是“新月传人”、“新月的最后一位旗手”。此言确否,历史自有公论。但梁实秋的文风,特别是他的为人,那恢宏的气度,风趣不失仁蔼,谑谑自有分寸的儒雅风范,对余光中影响深远。
由此,余光中正式开始他的文学之旅,七十年代他如日中天,虽未达“诸葛大名垂宇宙”之望,但真正地“光耀台湾”了。
此时的记忆对余光中来说,又像火车汽笛那样昂扬、激越。
后来,余光中与友人共同创办《蓝星诗社》杂志,参与现代诗的论战;再后来他“文化充军”,三度赴美,在爱荷华大学创作班深造;拜美国当代名诗人佛洛斯特为师……一路拾级而上,春风骀荡,终成大器,光耀中华。
余光中说他是“艺术的多妻主义者”。年少气盛时他自诩右手写诗,左手为文。他将第一部散文集冠名为《左手的缪思》,以彰显诗为正果,文为副业,评论、翻译为余事,皆隶属“第三只手”;此外他还钟情于绘画、音乐以及天文、地理、历史,乃至人类整个文化,好一个“千手观音”。其著译林林总总排列案头,犹如风光无限,满亭星月。
透视他的生活和家庭,亦可堪称星月满亭。
余光中在思想上是一位因循守旧的人。他不烟不酒,一杯茶足矣,过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机械得连吃饭都上固定的餐馆,点菜都是千篇一律。他是当年办《文学杂志》的朋友中唯一一个不上牌桌的人。他不想见那些不必见的人,因为他既不求官,也不竞选。对有共同旨趣的朋友,他盛情接纳,在香港七年,他的家几近成为台湾会馆,人称“沙田孟尝君”。对话不投机者,则三句嫌多,道不同不与为谋。但他确实又是一位冷面热心者,很会善解人意,乐于提携有才情的朋友与后学。
余光中文章写得好,人品又高尚,他晚年供职的高雄中山大学,校长把他当作镇校之宝,请他在运动衫、雨伞上题字,以赠来宾。在他退休后仍热情挽留,作为学校的“门脸”,每遇事不遂,一打余光中牌,便无往而不胜。而余光中自己“不喜欢在媒体上晃来晃去”,他是一位唯美主义者,追求心灵一片净土。
血永远浓于水。
第一位把余光中“引进”大陆的是诗人流沙河。80年代初,他俩通信,相互颇为欣赏对方的文采。流沙河本姓余,故互称“本家”。余光中在四川生活了八年,也算半个川娃。1986年,流沙河在一柄素扇上录了一阕《临江仙》辗转托送余光中,题词是“聊拂残暑”。余光中收到后马上回复:“时值溽暑,而清风在握,见者索阅,莫不称羡。”又惠诗《蜀人赠扇记》,有句云:“问我乐不思蜀吗?不,我思蜀而不乐。”后来,流沙河将此诗和相关资料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大陆读者始知海峡那边有个光耀中华的诗人余光中。
余光中和柯灵神交已久,他们还有一段难忘的友情。1988年的汉城国际笔会,余光中因故缺席。柯灵从上海带去一把宜兴茶壶准备相赠,后托请友人转交。余光中十分感动,作《宜兴茶壶》一诗答谢柯灵,诗中写道:“最清的泉水是君子之交/最香的茶叶是旧土之情/就这么举起空空的小壶/隔一道海峡犹如隔几/让我们斟酌两岸,品味古今”。真是一杯今日酒,万里故园心。
余光中这位望乡的牧神,对祖国的热爱,历来已久,珍藏在心中。早在他三十八岁(1966)壮年时,毫不忌讳地含泪写了遗嘱式的诗篇《当我死时》,诗中吟道:“当我死时/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用十七年未餍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鹧鸪的重庆,代替回乡”。且用余光中的诗作结:“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的中国”。
(编辑:姚天祥)



